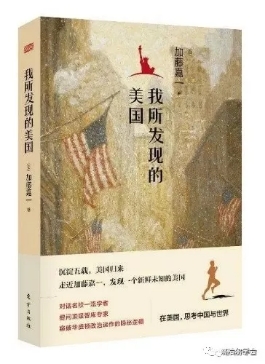
本文摘自著名日本旅华学者、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加藤嘉一的新著《我所发现的美国》(P102-108)。
加藤:您在新近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指出,“我们有必要聚焦于政治制度的出现、发展以及最终衰败的进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SAIS)的最近一期演讲中,您说道,“我不认为美国文明或私营产业正在走向衰落,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职能”。您或许会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正面临着通向衰败的潜在危机。我的问题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能从制度上避免这种衰败,而重获新生,甚至继续发展?在这个进程中,政府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您强调的“观念的力量”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福山:美国在早期历史上就经历过危机和衰败,比如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迎来工业经济兴起的时候,还有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那段时期。在这些例子中,危机最终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前者是由基层发起运动呼吁文官制度改革,最终推动了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的通过;后者则是罗斯福新政。然而,重建和复兴并不是自发的:它需要基层的动员,在上层具备好的领导,还要有催生政治行动的正确观念。目前我还没有在美国政治中看到任何这些要素,只是在左派和右派的部分选民中发现了一些愤怒情绪的雏形。现在最具权势的基层民众组织是茶党,不过他们的政策观点只会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弄得更糟。
加藤:我很好奇您如何从自由民主受到挑战的角度来考察“平等”这一主题。自由民主能够解决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吗?或者说自由民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负责?在政治体制内部,有没有什么必要的制度性努力或改革?
福山:我认为,不平等的增加和中产阶级的衰落是当下的民主面临的最大问题。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体对于民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拥有大量的穷人和少数寡头统治者,就像拉丁美洲一样,这里的政治就会在因循守旧的统治和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如今的问题在于,不平等根本上是由科技进步所驱使的。智能化机器正在(先是缓慢地,然后迅速地)取代熟练工人。在美国,未来的职业会在两种类型之间产生分化:一种是报酬低、技能含量低的职业,比如健康护理;另一种是高技术要求的职业,如编程员、银行家,诸如此类。这不是一个专属于民主社会的问题,但是民主的稳定性有赖于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因而这一点上特别危险。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可靠的解决方案。
加藤:对我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和宗教如今都在谈论政府(或是国家)的地位。无论是欧洲、日本的经济危机,还是中东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都应重新思考政府(或是国家)应该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从您研究的角度出发,政府角色的核心是什么?我知道在不同的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我想听一听您从您的理论谈谈对现实的理解。
福山:世界上的很多政府都被认为是脱离选民的,它导致的后果是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盛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政府的规模上,而是出在政府的执政能力上:政府应该对公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敏捷的反应,并且灵活地运用新路子处理它们。在很多国家,政客过度依赖于强大有序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不能代表全体公民的愿望。
加藤:说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它对公民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这两种能力?美国政治能从中国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吗?
福山:如果从结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胜任的。比如说,政府为了发展乡镇企业落实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这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说,政府剥夺了军队从事营利的生意。然而,中国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腐败问题。我们无法从经验上准确获知腐败的程度,也无法和其他国家做比较;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着手进行研究的主题。
加藤:您如何从“历史的终结”的角度来评价苏联解体后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何能够在未来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
福山: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挑战。你的问题在于:长远来看,这个体制是否可持续。会有很多理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它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时——这些社会压力的出现是现代化的产物——就会遇到大量挑战。不过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这些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加藤:所谓“中国模式”似乎有一种传播开来的趋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国家感觉这种模式对它们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国家构建具有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意图地向这些国家或区域为这种模式“做广告”,旨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范围。我想这一举措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西方自由民主具备怎样的修复能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福山:很多人想要复制中国模式,但是他们无法复制中国模式中其他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精英制,一个高度纪律化的政党层级,对教育的尊重,还有之前所说的,领导人中具备的一种意识,那就是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特定责任感。所有亚洲威权政制的统治者或多或少都具备这种特质,他们关心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而这些特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东或非洲的统治者身上是缺失的。
加藤:在您的新书中,您对于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尤为关注。您提到:“在中国,确立一种能够限制政治权威的法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您能具体谈下吗?
福山:中国近些年一直在推行“基于法治的决策制定”,这意味着基层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约束。但是真正的法治需要将法律和政治体制中最具权势的行动者结为一体。法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指——统治从属于法律。
加藤:您一直在从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行为举止中探讨它们如何对中国的政治做出改变,我很赞赏您的这一努力。我也非常同意您在最近这本书中的观点:“中国法治和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新的社会群体能否打破传统的力量均衡,这种力量一直存在于中国过去的国家和社会之中。”。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亿万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发展不太热心,他们一辈子可能都只在社会层面有所需求,比如教育、住宅、卫生保健等一些现在的政治体制可以提供的东西。此外,中产阶级似乎也不认为问责制民主会比“复杂的官僚制”运行得更好,“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替代选择了”。我认为这些都反映出当今中国人的国家主义。
福山:我认为,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增长,中产阶级就会乐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是相当困难的,面对经济不景气甚至是经济衰退,当收入降低或就业率下降之时,中产阶级又会作何感想呢?
加藤:我发现近些年来,尤其是在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相当多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褒奖”,这不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自身有多好,而是自由民主制在问题的解决上已经走向了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民主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自由民主如何改进自身,特别是改进问题解决的能力,否则国家主义将会抬头,成为某种“负责任的”体制,其结果就是,自由民主相应地走向衰落。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福山:对,我认为不同的体制可见的成功或失败对于其他国家在观念和体制类型上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现在的危险在于,一些体制看上去运转良好,与此同时,诸如美国、欧盟、日本等民主国家则深陷低增长或失业状态。所以说对这些国家的精英而言,尤其要对政治改革的问题多加留意,它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